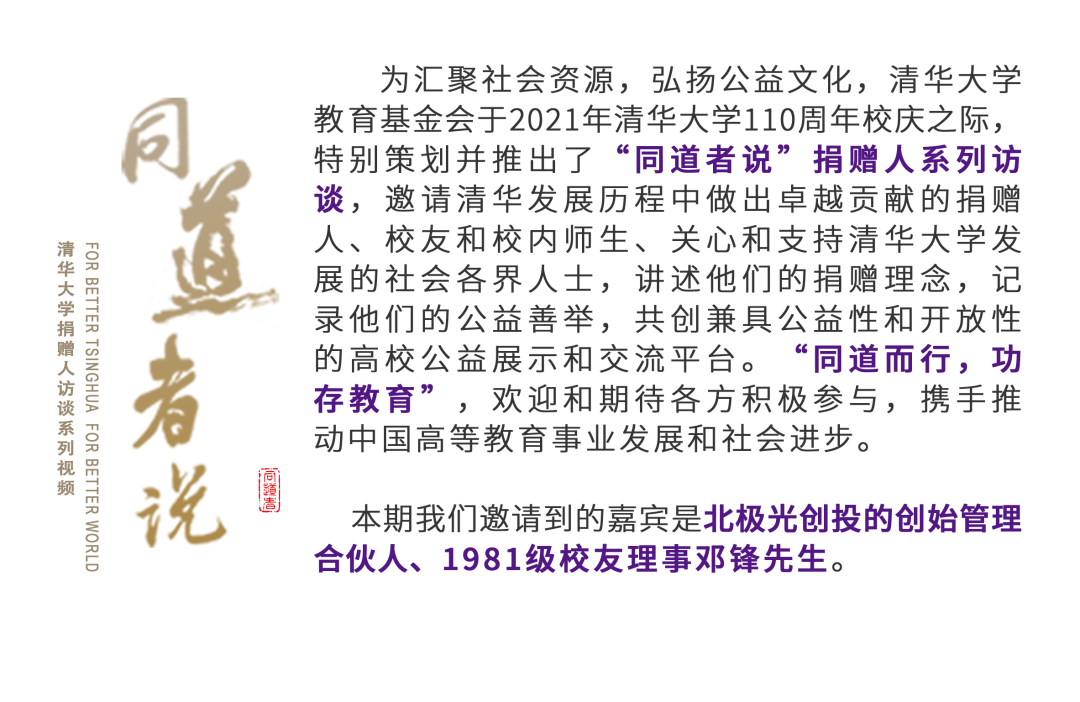
您曾多次捐赠支持清华大学人才培养,还记得自己捐赠的第一个项目吗?
邓锋:当然记得,那是2004年,我第一个捐赠的项目是支持清华大学信息学院的学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主要内容是支持学生出国一周期间的飞机票、酒店、餐饮、会议注册费等,大约每年资助100个学生,从2004年至今已有1700多人次受益。

2006年,邓锋校友与“信息学院人才引进及研究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基金”受助学生合影
邓锋: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举办地在国外的一个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但因为我当时没有钱,所以去不了。当时的切身体会就是,好论文写出来了但是因为资金不足学生不能做国际展示和交流,这个令人遗憾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我的项目初心。
有意思的是,我最初觉得这样做可以帮助清华的学生们更有动力去写好论文,也可以提高清华大学国际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后来项目受益学生给我的反馈是,他们最大的收益是借助第一次出国开了眼界,了解了如何做国际学术交流,如何与外国人沟通,也见识了异域的风土人情等,这些成为他们人生第一次出国最大的收获。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也很欣慰。
邓锋:过去给到清华的捐助多用在不动产比如说盖楼。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人”身上。直到2020年之前我给清华的捐助全是各类人才培养项目,这与我的亲身经历也有关:在学业方面我曾在国外多所大学深造,在工作中我通过运营管理建议帮助商业项目取得成功。所以我把自己的捐赠重点聚焦在人才培养上。
捐赠持续将近20年,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持续支持清华大学及教育基金会发展?
邓锋:在捐赠项目运作方面,我们都是按照商业运营的方法来做非营利的事情。项目起步阶段有详细计划,每个项目均有专人负责,并进行KPI考核管理。以一个十年期项目为例,采取“1+2+7”的方式进行管理,即第一年先拨付一年的资金,年底进行评估总结,如果项目做得好再给两年的资金;如果两年后项目依然成功,再给七年的资金。这种做法可以保证项目按照计划推进,运营管理颗粒度很细,有助于项目取得成功。
为什么我捐赠和支持的项目越来越多呢?因为从第一个项目开始到后来所有的项目,无论是项目意义和价值,还是项目执行实际效果,我发现钱花得很值,都用在了刀刃上,可以说形成了良性循环,那我就会继续做下去。
作为理事,您是如何帮助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劝募的?
邓锋:我作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理事,会跟一些有捐赠意愿的人进行沟通交流。普遍来讲,毫无疑问大家会说清华大学是中国一流的顶尖大学,但具体来看,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每个人想做的事情不一样。如果只是说“捐给清华,我们把你们的钱用好”,仅有这个口头承诺还不够。
首先要提前准备拟劝募的项目列表,沟通的时候了解对方的兴趣点,告诉对方捐赠何种项目会带来相应的何种变化,帮助捐赠人找到适合其个人的项目。
第二,我会分享自己的项目捐赠经历和切身体验,清华大学基金会的秘书处团队本身具有优秀的项目执行力,通过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来获得捐赠人的信任,也会触发连续捐赠和长期支持。
2007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时任理事长贺美英和邓锋校友参加登峰基金座谈会
您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同时见证了中国高校基金会的发展,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看到的变化以及未来将面对的挑战吗?
邓锋:首先是捐款总金额大幅增加。第二,捐款人的背景有很大的变化,过去主要靠港台老一辈的成功企业家们,现在更多的是清华校友,而且比较多的是年轻的校友企业家,目前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捐赠人的主体。第三,善款用途也比以前更加丰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最早的用途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现在的善款用途比较多元化,比如用到人身上,而且也不局限于过去单一发奖学金的方式,比如支持清华某些学生社团、某场比赛、某个领导力培训营、某些方面的研究。第四,捐款投资管理和保值增值工作日趋专业化,拓宽了基金会的收入来源和资金渠道。
以前是“捐给清华”,现在是“捐在清华,服务社会”。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转变呢?
邓锋:过去的思路比较窄,现在的捐赠辐射面更广,表面看资金捐给了清华,但实际上清华将善款通过项目转化最终服务于社会。举例来说,盖茨基金会跟清华大学合作建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受益对象不仅是清华大学,也不仅是中国,而是全球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
2017年,邓锋将投资兆易创新的股权变现后悉数捐赠给清华,清华大学时任校长邱勇(中)与邓锋合影
您曾经谦逊地说,成功很大程度是靠运气。那么,影响您选择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邓锋:首先真的不是谦逊,而是实事求是,发自内心的这么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当然自己也要努力,要有足够的智慧,运气来的时候才能紧紧抓住机会。
我经常说自己的性格是“大事胆大,小事胆小”,在选择关键方向时,不能等到做数据分析和研究,因为等到数据分析研究全了这个事就太晚了,要做决定就要早做,而这种决定是靠自己的感觉和过去经验的积累。而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比如一家企业该不该投资,我和团队可能要做很多很详尽的数据分析,要很仔细的去看,这个属于“小事胆小”,要做得谨慎一点。
邓锋:我没有觉得这是特别需要我去思考很久才能做出的决定,我在2004、2005年的时候就考虑回国,当时回国是很自然的事,那时我已经挺清楚的看到,中国的机会更大,无论是国家还是我个人。而且在熟悉的文化、熟悉的人当中,自己能发挥的空间也更多,生活环境也更适应。
邓锋:其实捐赠也是一种投资,基本逻辑是一样的,都要选择好的项目,即价值的发现和价值的增加,希望花出去的钱有回报。但在回报方式上二者却有显著的不同,商业投资的回报方式一般是资金,而捐赠的回报方式往往是正面的社会效果。
2019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25周年座谈会上,与清华大学时任党委书记陈旭合影
您曾说,下半辈子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有意义和更多承担社会责任的事情上,您现在觉得做得如何呢?
邓锋:我觉得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做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这让我很快乐。I cannot afford not being happy.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我觉得现在挺好,要问我以后的目标是什么?我以后的目标就是像现在这样活着。
